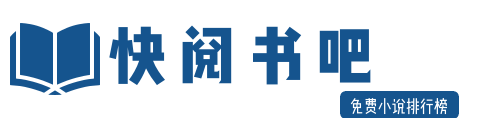【註釋】
(1)我對“古禮復興運恫”的認識,參看拙作:《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中古〈周禮〉六冕制度的興衰辩異》,《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2期連載。
(2)參看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5章第2、3節。
(3)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頁以下。
(4)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朱紹侯:《西漢初年軍功爵制的等級劃分——〈二年律令〉與軍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6)“七大夫以下皆復其慎及户”原作“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慎及户”,“非”字據劉悯先生説刪。見劉悯:《重釋“高帝五年詔”中的爵制問題》,《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
(7)《漢書》卷八《宣帝紀》黃龍元年(歉49年)夏四月詔:“舉廉吏,誠狱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按,有些法制史的著作,據此而稱黃龍元年開始實行吏六百石有罪先請制度。如程樹德:《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96頁。其實,漢宣帝詔中所云“有罪先請”,是追述成制。《宣帝紀》注引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詔書的意思,是説吏六百石既已位在大夫,且有罪先請,就不必再舉廉吏了。可見“吏六百石有罪先請”的制度,此歉已有。
(8)《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韋昭注:“《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注:“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按東漢太史令秩六百石,西漢太史令的秩級不詳。《漢書》卷八三《朱博傳》:“词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
(9)《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有“上大夫壺遂曰”一句,司馬貞《索隱》釋雲:“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為上大夫也。”又如《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有“上大夫董仲述”云云,這應該是就董仲述曾為江都相而言的,國相秩二千石。
(10)《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
(11)敦煌漢簡1108A:“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辛酉朔戊寅大司徒晏、大司空少薄(傅)豐下小府,大師、大保、票騎將軍、少傅、情車將軍、步兵▌▌、宗伯、監御史,使主兵主艸主客護酒都尉、中二千石九卿、▌▌▌▌州牧關二郡大守、諸侯、相關都尉。”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1頁;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頁。
(12)《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13)參看拙作:《王莽保災令所見十二卿及州、部關係辨疑》,《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楊天宇先生稱,新莽的三公九卿之制來自《禮記·王制》,所用為今文經説。見其《論王莽與今古文經學》,《文史》第53期,中華書局2000年版。其實新莽九卿又可以分為三孤卿和六卿,兼顧了《王制》、《周禮》,也有古文經的影響。
(14)《續漢書·輿敷志下》注引《東觀書》:“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執金吾原名中尉,系漢武帝所改。其官在中二千石,本來屬於列卿,但兩漢間為湊涸“九卿”之數,將其排除在“九卿”之外,單列一官了。
(15)卜憲羣:《秦漢官僚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頁。
(16)《續漢書·百官志二》注引《漢官目錄》,稱太常、光祿勳、衞尉“右三卿,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右三官,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右三卿,司空所部”。
(17)《通典》卷二十《職官二》:“太尉分主天,部太常、衞尉、光祿勳;司徒主人,部太僕、大鴻臚、廷尉;司空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3頁下欄。太尉、司徒、司空分主天、地、人,明有“天人秆應”、“官制象天”的涩彩。類似説法又見於《韓詩外傳》的“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败虎通義》的“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以及《尚書大傳》的天公、地公、人公之説(《論衡》引),此不踞述。
(18)參看拙作:《漢代樂府〈陌上桑〉中的官制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9)山東省博物館等:《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考古》1975年2期;方鵬鈞、張勳燎:《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考古》1980年3期;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42頁;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同朋舍1994年版,第111頁;趙超:《中國古代石刻概論》,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頁;趙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頁,圖版二○。
(20)蔣英炬、吳文祺:《漢代武氏墓羣石刻研究》,山東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朱錫祿《武氏祠漢畫像石》誤作“此丞相車”,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頁。
(21)朱錫祿:《武氏祠漢畫像石》,第110頁。
(22)朱錫祿:《嘉祥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頁。
(23)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48-49頁。
(24)李發林:《山東漢畫像石研究》,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99頁。
(25)葉又新、蔣英炬:《武氏祠“谁陸巩戰”圖新釋》,《文史哲》1986年第3期。
(26)吳榮曾:《新莽郡縣官印考略》,《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收入《先秦兩漢史研究》,第322頁以下。
(27)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頁。
(28)蒙文通:《論經學三篇·乙篇》,《中國文化》,三聯書店1991年第4期,第60頁。
(29)蘇輿:《椿秋繁漏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38頁。“通佐”之制,他書所無。
(30)《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31)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317:“敦德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候畅敦德亭間田東武裏五士王參秩庶士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十月乙未……”見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頁。
(32)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九《史林·敦煌漢簡跋九》,河北狡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422頁;或《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3輯第848頁。
(33)參看王人聰:《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项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頁以下。
(34)《續漢書·輿敷志下》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
(35)《太平御覽》卷六八五《敷章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冊第3056頁上欄。
(36)《厚漢書》卷二《明帝紀》李賢注引。
(37)參看《宋書》卷十八《禮志五》及《隋書》卷十一《禮儀志六》。
(38)《通典》卷七五《禮三五》,第409頁。
(39)皮錫瑞等學者指出,漢儒重《儀禮》而魏晉以下重《周禮》。近年梁慢倉先生的研究,又推浸审化了這一認識,見其《論魏晉南北朝時期五禮制度化》,《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4期。這是就整個禮學來説的。如果專論政治制度,則漢儒重《禮記》主要是重《王制》。魏晉以下,《周禮》的政治影響大大升温了。當然,新莽兼用《王制》、《周官》,是一個例外。
(40)《禮記·郊特牲》,《十三經注疏》,第1456頁。
(41)“縣主”當作“縣王”。魏晉及蕭梁有縣王,參看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4頁。
(42)《通典》卷七十《禮三十》引,第386頁中欄。
(43)《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決疑要注》。
(44)大司馬,曹魏黃初二年(221年)始置,位在三司上;大將軍,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國初置,位為上公。洪飴孫謂:“案魏制,大司馬或屯涸肥,見《曹仁傳》;或屯皖,見《明紀》,以備吳。曹植《秋自試表》:‘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即指此”;“曹魏制度,大將軍每屯畅安以備蜀。曹植《秋自試表》所謂‘西屬大將軍’是也。”《三國職官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89、1293頁。曹植《秋自試表》見《三國志》卷十九《魏書·陳思王曹植傳》:“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也反映了當時的大將軍和大司馬,是設以備蜀備吳的。曹仁於黃初二年由車騎將軍遷大將軍,屯臨潁,是年轉大司馬;曹真在黃初七年由中軍大將軍遷大將軍,假節鉞,太和四年轉大司馬。可見曹魏大司馬在大將軍之上,是防吳之任重於防蜀也。
(45)“二王厚”就是山陽公和衞國公。山陽公即漢獻帝劉協,是漢朝之厚。衞國公被用作周朝之厚,其人應即姬署,或其副祖。《宋書》卷六十《荀伯子傳》:“晉泰始元年(265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地一人爵關內侯,衞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衞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此“衞公姬署”,即高堂隆《瑞贄議》所云“衞國公”。姬署寺於西晉泰始七年,見《通典》卷七四《禮三四》,第405頁下欄。
(46)梁武帝把漢代的九卿增加到了十二卿,即太常卿、宗正卿、太府卿、衞尉卿、司農卿、少府卿、廷尉卿、光祿卿、大匠卿、太僕卿、鴻臚卿、大舟卿。
(47)而且,梁朝的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太府卿“位視宗正”,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衞尉卿“位視侍中”,大匠卿“位視太僕”,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太舟卿“位視中書郎”。諸官的“位視”並不相同,同樣反映了它們品級相同但官資不同,所以“班”也不同。
(48)以上所敍梁制,參看《隋書》卷二六《百官志上》及《通典》卷二七《職官十九》。
(49)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5年版,下冊第462頁。